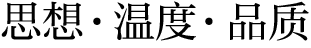图米纳斯:将涌动的心声奏成轰鸣
北京青年报
2025-09-11 03:00

010
◎栗征
契诃夫是里马斯·图米纳斯十分钟爱的剧作家,在他辉煌的导演生涯中,《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占据了重要篇章。其中,《万尼亚舅舅》是图米纳斯就任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艺术总监后第一部取得轰动性成功的作品。
这部《万尼亚舅舅》近日于中国上演。继《马达加斯加》《假面舞会》《叶甫盖尼·奥涅金》《战争与和平》等之后,中国观众又一次现场领略图米纳斯高超而迷人的舞台艺术。



 呈现契诃夫的悖反性
呈现契诃夫的悖反性
不是件容易的事
契诃夫的戏剧不易理解,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很少描绘单面、确定且清晰的人物性格和思想,呈现的常是不同声音的平等对话、多重情绪的交织渗透、悲喜因素的杂糅融合,而且彼此矛盾的成分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物的灵魂之中。
在《万尼亚舅舅》中,教授谢烈勃利亚科夫的形象看似扁平,跟随着万尼亚舅舅的视角,我们很容易对他产生这样的印象:虚伪、自私、冷酷、倨傲。他不仅在学术上欺世盗名,而且对20多年来为他无私奉献的万尼亚舅舅毫无感恩之情;退休搬进乡间庄园后,把这里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一团糟。
教授固然可恶,契诃夫却对他不乏同情。在第二幕的那个风雨交加之夜,契诃夫着重刻画了这个“暴君”脆弱的一面——他不得不苦苦忍受衰老和孤独的折磨。教授真的像万尼亚舅舅指责的那般不堪吗?不少学者并不这么认为。丹麦学者凯尔德·比约纳格甚至推断,教授曾经是进步社会思想的支持者。
医生阿斯特罗夫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是一个身体力行保护森林、承担起对全人类和后代子孙之责任的实干知识分子中,叶莲娜对他的赞美——“勇敢的精神,自由的头脑,宏大的气魄”,并未夸大其词。森林可以唤起人们的崇高情感,医生对此深信不疑,然而这一信条无法被他自身证实。《万尼亚舅舅》的第一场戏就是医生向老奶妈倾诉苦恼,他一方面厌恶乏味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不满自己的日渐麻木。他沉湎于叶莲娜的美貌,但又清楚地知道,这种感情是浅薄庸俗的,绝非严肃的、真正的、有价值的爱。
在舞台演出中呈现契诃夫戏剧的种种悖反性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图米纳斯导演的《万尼亚舅舅》中,最突出地表现契诃夫戏剧这一特性的,莫过于第三幕万尼亚舅舅向教授开枪的情节高潮。这场戏如果过于严肃,就会淹没契诃夫埋藏其间的嘲讽;如果完全排成闹剧,又会冲淡浓烈的悲剧感。从教授开始讲话起,图米纳斯接二连三地动用喜剧手段:先是教授并不好笑的玩笑引来他的忠实崇拜者玛丽雅长时间的笑声;随后,对于教授出售田产的提议,万尼亚舅舅越来越无法保持冷静,愤怒到似乎被抽空了全部力气,他抓着教授,头顶在教授身上,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厮打起来。
随后,万尼亚舅舅激动地走下舞台,他不在台上的这段时间,教授和叶莲娜爱抚、拥抱、接吻。后台传来一声枪响,全剧最滑稽的场面出现了:持枪上台的万尼亚舅舅试图转枪耍帅,可动作十分笨拙;他拉开先后挡在教授身前的叶莲娜和玛丽雅,后退,举枪,仿佛这是一场正式的决斗;教授撩开外套,昂首挺胸,看上去视死如归;一声枪响,教授岿然不动,万尼亚舅舅感到不可置信,上前查看教授的身体,教授将万尼亚舅舅一把推倒。
音乐响起,排成一行的人们仪式性地于舞台前后折返,万尼亚舅舅陷入悲痛。在他开枪之前,图米纳斯已经做出暗示,这是一次注定徒劳的反抗。此处,被滑稽化的不仅仅是万尼亚舅舅此次的失败,他的整个前半生都沦为了笑话。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这难道不可悲吗?一个人意识到他虚度光阴,可是为时已晚,这难道不可笑吗?契诃夫是刻薄的,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在他眼中是带有喜剧性的,悲剧和喜剧不过是一体两面。当悲喜熔铸于同一个舞台场面,巨大的情感与美学能量从中诞生。
突破语言的极限
艺术开始翩翩起舞
对戏剧人物的内心进行有效的舞台外化,是戏剧导演的必备技能。而排演契诃夫戏剧的难度不仅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外化。“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这是契诃夫的创作箴言。如何在演出中揭示看似平常的一刻对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如何把那些难以言表的悲伤或愉悦化作舞台上的视觉形象和听觉效果?图米纳斯的舞台像一台扩音器,把剧中人涌动的心声以最高分贝变成轰鸣。
第二幕中,天气的变化映衬着人物情绪的流动。开幕时,大雨将至,风把窗子吹得砰砰作响,教授喋喋不休地抱怨着,气氛凝重压抑。雨下起来了,万尼亚舅舅的示爱又一次被叶莲娜拒绝,他懊恼地回忆着往事,痛感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雨渐渐小了,阿斯特罗夫向索尼娅敞开心扉,他的话激起了索尼娅对幸福的期待,抒情的调子开始冲破烦闷的包围圈。雨过天晴,索尼娅和叶莲娜言归于好,空气中充溢着喜悦,欢快的情绪攀升到这一幕的顶点。
然而,教授残忍地破坏了她们想要弹钢琴的愿望,整幕戏的情绪运动曲线骤然从最高点降至最低点。图米纳斯此时的处理是:索尼娅和叶莲娜坐在落满灰尘的钢琴前,她们的手指重重地砸在琴键上,索尼娅扭头看向观众,叶莲娜抬手用力按住钢琴顶盖,钢琴声被“消音”,二人定格。她们几次重复这套动作——其实在大音量的配乐中,钢琴声无论如何都会被淹没。图米纳斯的设计完美地传达出契诃夫的意图,既表现了索尼娅和叶莲娜对幸福与自由的渴求,又对她们的美好愿望遭到扼杀发出悲鸣。
契诃夫戏剧通常在第三幕出现人物情感的集体爆发。《万尼亚舅舅》第三幕中,几个主要人物都经历了剧烈的情感震荡。索尼娅在这一幕迎来了爱情的死亡宣判。在舞台上,急于知道医生如何答复的索尼娅冲向叶莲娜,此时的叶莲娜还在因为医生的粗鲁举动神昏意乱,万尼亚舅舅阻隔在二人之间将索尼娅拦住。索尼娅奋力伸手够向叶莲娜,长工上场,抱起索尼娅,向台后走去。索尼娅挣脱,跑回台前,举起双手,试图在空气中抓住些什么。长工再次抱起索尼娅,索尼娅再次挣脱,重复抓向虚空的动作。
我们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已经见识过,没有什么比身体姿态更能表明恋爱之人的绚烂情感,更能展现爱情的原始冲动。而索尼娅这一动作的妙处不仅在于无望爱情的能量宣泄,更在于“抓空”姿势的象征意义——《万尼亚舅舅》最令人心碎之处正在于幸福在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悄然溜走。
在图米纳斯的舞台上,当需要突破语言的表意极限时,艺术开始翩翩起舞。
安放统摄全剧的意象
隐喻瞬间与永恒对峙
在《万尼亚舅舅》全剧开始之前,叶莲娜的精神幻灭已经发生,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青春被埋葬在对教授的不真实爱情中,她才会失去生活热情,表现出慵懒之态。而在剧中,万尼亚舅舅、阿斯特罗夫和索尼娅也都经历了沉痛的精神幻灭。第四幕,契诃夫为幻灭后的他们选择了有别于叶莲娜的生活道路。
教授夫妇离开庄园后,阿斯特罗夫也要和他的朋友们告别。契诃夫给临行前的医生写下一句令人费解的台词:“(走到非洲地图跟前,瞧着它)大概在这个非洲,现在热得要命。”高尔基对这句台词大加赞赏,他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当医生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静场之后说起了非洲的炎热时,我颤栗了——我为您的才华颤栗,我为对于人,对于我们那乏味的、灰色的生活的恐惧而颤栗。您是如此有力而准确地击中我们的灵魂!”高尔基的意思是,非洲指向对此处灰色生活的逃离,而当医生说出这句话时,逃离的可能性已离他远去。
图米纳斯让阿斯特罗夫以一个奇异的造型说出这句奇特的台词——他的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以及他向叶莲娜展示地图时使用的脚架。扛着重负的他一边慢慢后退,一边像动物一般仰头长啸。这是一个与《海鸥》第四幕的尼娜相近的艺术形象,阿斯特罗夫必须背负起属于他自己的十字架。
医生离开了,舞台上只剩下万尼亚舅舅和索尼娅。现在,他们只有依靠无休无止的工作才能对抗生存的虚无。索尼娅极力忍住悲伤,说出本剧最著名的那段独白。最后,万尼亚舅舅如行尸走肉般退场,索尼娅仰卧在工作台上。灯光逐渐扩大照射范围,点亮大半个舞台,但索尼娅被遗留在黑暗中。这似乎是在表明,索尼娅将在死后的世界里看到“布满钻石的天空”。
图米纳斯又一次展现出他把希望与哀伤交融于同一场面的非凡能力。索尼娅对光明的期待、对未来的信念,不能否定万尼亚舅舅当下的痛苦;万尼亚舅舅生命意义的丧失,亦不能否定索尼娅的隐忍和奉献蕴含着的神圣性与超越性。契诃夫对“应当如何生活”的深邃思考,在图米纳斯的诗意与梦幻中浮现。
不同于《海鸥》中的“海鸥”、《三姐妹》中的“莫斯科”、《樱桃园》中的“樱桃园”,契诃夫并未在《万尼亚舅舅》中设置一个统摄全剧的意象。图米纳斯在舞台后部放置了一座狮子雕像,它自始至终不曾被移动,或许表征着图米纳斯对《万尼亚舅舅》的总体性印象。俄罗斯评论界一般将这座雕像理解为某种历史荣耀或是权力,剧中人和它的并置,隐喻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之间的对峙。演出谢幕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那头狮子是图米纳斯的在天之灵,默默守护着舞台;它也是契诃夫的在天之灵,带着冷峻的微笑,提醒我们以信仰和勇气对抗生活中的种种蒙昧与荒谬。
契诃夫是里马斯·图米纳斯十分钟爱的剧作家,在他辉煌的导演生涯中,《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占据了重要篇章。其中,《万尼亚舅舅》是图米纳斯就任俄罗斯瓦赫坦戈夫剧院艺术总监后第一部取得轰动性成功的作品。
这部《万尼亚舅舅》近日于中国上演。继《马达加斯加》《假面舞会》《叶甫盖尼·奥涅金》《战争与和平》等之后,中国观众又一次现场领略图米纳斯高超而迷人的舞台艺术。



 呈现契诃夫的悖反性
呈现契诃夫的悖反性不是件容易的事
契诃夫的戏剧不易理解,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他很少描绘单面、确定且清晰的人物性格和思想,呈现的常是不同声音的平等对话、多重情绪的交织渗透、悲喜因素的杂糅融合,而且彼此矛盾的成分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物的灵魂之中。
在《万尼亚舅舅》中,教授谢烈勃利亚科夫的形象看似扁平,跟随着万尼亚舅舅的视角,我们很容易对他产生这样的印象:虚伪、自私、冷酷、倨傲。他不仅在学术上欺世盗名,而且对20多年来为他无私奉献的万尼亚舅舅毫无感恩之情;退休搬进乡间庄园后,把这里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一团糟。
教授固然可恶,契诃夫却对他不乏同情。在第二幕的那个风雨交加之夜,契诃夫着重刻画了这个“暴君”脆弱的一面——他不得不苦苦忍受衰老和孤独的折磨。教授真的像万尼亚舅舅指责的那般不堪吗?不少学者并不这么认为。丹麦学者凯尔德·比约纳格甚至推断,教授曾经是进步社会思想的支持者。
医生阿斯特罗夫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是一个身体力行保护森林、承担起对全人类和后代子孙之责任的实干知识分子中,叶莲娜对他的赞美——“勇敢的精神,自由的头脑,宏大的气魄”,并未夸大其词。森林可以唤起人们的崇高情感,医生对此深信不疑,然而这一信条无法被他自身证实。《万尼亚舅舅》的第一场戏就是医生向老奶妈倾诉苦恼,他一方面厌恶乏味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不满自己的日渐麻木。他沉湎于叶莲娜的美貌,但又清楚地知道,这种感情是浅薄庸俗的,绝非严肃的、真正的、有价值的爱。
在舞台演出中呈现契诃夫戏剧的种种悖反性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图米纳斯导演的《万尼亚舅舅》中,最突出地表现契诃夫戏剧这一特性的,莫过于第三幕万尼亚舅舅向教授开枪的情节高潮。这场戏如果过于严肃,就会淹没契诃夫埋藏其间的嘲讽;如果完全排成闹剧,又会冲淡浓烈的悲剧感。从教授开始讲话起,图米纳斯接二连三地动用喜剧手段:先是教授并不好笑的玩笑引来他的忠实崇拜者玛丽雅长时间的笑声;随后,对于教授出售田产的提议,万尼亚舅舅越来越无法保持冷静,愤怒到似乎被抽空了全部力气,他抓着教授,头顶在教授身上,两个人像小孩子一样厮打起来。
随后,万尼亚舅舅激动地走下舞台,他不在台上的这段时间,教授和叶莲娜爱抚、拥抱、接吻。后台传来一声枪响,全剧最滑稽的场面出现了:持枪上台的万尼亚舅舅试图转枪耍帅,可动作十分笨拙;他拉开先后挡在教授身前的叶莲娜和玛丽雅,后退,举枪,仿佛这是一场正式的决斗;教授撩开外套,昂首挺胸,看上去视死如归;一声枪响,教授岿然不动,万尼亚舅舅感到不可置信,上前查看教授的身体,教授将万尼亚舅舅一把推倒。
音乐响起,排成一行的人们仪式性地于舞台前后折返,万尼亚舅舅陷入悲痛。在他开枪之前,图米纳斯已经做出暗示,这是一次注定徒劳的反抗。此处,被滑稽化的不仅仅是万尼亚舅舅此次的失败,他的整个前半生都沦为了笑话。一个人的生命被白白浪费了,这难道不可悲吗?一个人意识到他虚度光阴,可是为时已晚,这难道不可笑吗?契诃夫是刻薄的,人类难以克服的弱点在他眼中是带有喜剧性的,悲剧和喜剧不过是一体两面。当悲喜熔铸于同一个舞台场面,巨大的情感与美学能量从中诞生。
突破语言的极限
艺术开始翩翩起舞
对戏剧人物的内心进行有效的舞台外化,是戏剧导演的必备技能。而排演契诃夫戏剧的难度不仅在于一般意义上的心理外化。“在舞台上得让一切事情像生活里那样复杂,同时又那样简单。人们吃饭,仅仅吃饭,可是在这时候他们的幸福形成了,或者他们的生活毁掉了。”这是契诃夫的创作箴言。如何在演出中揭示看似平常的一刻对命运的决定性意义?如何把那些难以言表的悲伤或愉悦化作舞台上的视觉形象和听觉效果?图米纳斯的舞台像一台扩音器,把剧中人涌动的心声以最高分贝变成轰鸣。
第二幕中,天气的变化映衬着人物情绪的流动。开幕时,大雨将至,风把窗子吹得砰砰作响,教授喋喋不休地抱怨着,气氛凝重压抑。雨下起来了,万尼亚舅舅的示爱又一次被叶莲娜拒绝,他懊恼地回忆着往事,痛感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雨渐渐小了,阿斯特罗夫向索尼娅敞开心扉,他的话激起了索尼娅对幸福的期待,抒情的调子开始冲破烦闷的包围圈。雨过天晴,索尼娅和叶莲娜言归于好,空气中充溢着喜悦,欢快的情绪攀升到这一幕的顶点。
然而,教授残忍地破坏了她们想要弹钢琴的愿望,整幕戏的情绪运动曲线骤然从最高点降至最低点。图米纳斯此时的处理是:索尼娅和叶莲娜坐在落满灰尘的钢琴前,她们的手指重重地砸在琴键上,索尼娅扭头看向观众,叶莲娜抬手用力按住钢琴顶盖,钢琴声被“消音”,二人定格。她们几次重复这套动作——其实在大音量的配乐中,钢琴声无论如何都会被淹没。图米纳斯的设计完美地传达出契诃夫的意图,既表现了索尼娅和叶莲娜对幸福与自由的渴求,又对她们的美好愿望遭到扼杀发出悲鸣。
契诃夫戏剧通常在第三幕出现人物情感的集体爆发。《万尼亚舅舅》第三幕中,几个主要人物都经历了剧烈的情感震荡。索尼娅在这一幕迎来了爱情的死亡宣判。在舞台上,急于知道医生如何答复的索尼娅冲向叶莲娜,此时的叶莲娜还在因为医生的粗鲁举动神昏意乱,万尼亚舅舅阻隔在二人之间将索尼娅拦住。索尼娅奋力伸手够向叶莲娜,长工上场,抱起索尼娅,向台后走去。索尼娅挣脱,跑回台前,举起双手,试图在空气中抓住些什么。长工再次抱起索尼娅,索尼娅再次挣脱,重复抓向虚空的动作。
我们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已经见识过,没有什么比身体姿态更能表明恋爱之人的绚烂情感,更能展现爱情的原始冲动。而索尼娅这一动作的妙处不仅在于无望爱情的能量宣泄,更在于“抓空”姿势的象征意义——《万尼亚舅舅》最令人心碎之处正在于幸福在人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悄然溜走。
在图米纳斯的舞台上,当需要突破语言的表意极限时,艺术开始翩翩起舞。
安放统摄全剧的意象
隐喻瞬间与永恒对峙
在《万尼亚舅舅》全剧开始之前,叶莲娜的精神幻灭已经发生,由于意识到自己的青春被埋葬在对教授的不真实爱情中,她才会失去生活热情,表现出慵懒之态。而在剧中,万尼亚舅舅、阿斯特罗夫和索尼娅也都经历了沉痛的精神幻灭。第四幕,契诃夫为幻灭后的他们选择了有别于叶莲娜的生活道路。
教授夫妇离开庄园后,阿斯特罗夫也要和他的朋友们告别。契诃夫给临行前的医生写下一句令人费解的台词:“(走到非洲地图跟前,瞧着它)大概在这个非洲,现在热得要命。”高尔基对这句台词大加赞赏,他在给契诃夫的信中写道:“当医生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静场之后说起了非洲的炎热时,我颤栗了——我为您的才华颤栗,我为对于人,对于我们那乏味的、灰色的生活的恐惧而颤栗。您是如此有力而准确地击中我们的灵魂!”高尔基的意思是,非洲指向对此处灰色生活的逃离,而当医生说出这句话时,逃离的可能性已离他远去。
图米纳斯让阿斯特罗夫以一个奇异的造型说出这句奇特的台词——他的身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箱子以及他向叶莲娜展示地图时使用的脚架。扛着重负的他一边慢慢后退,一边像动物一般仰头长啸。这是一个与《海鸥》第四幕的尼娜相近的艺术形象,阿斯特罗夫必须背负起属于他自己的十字架。
医生离开了,舞台上只剩下万尼亚舅舅和索尼娅。现在,他们只有依靠无休无止的工作才能对抗生存的虚无。索尼娅极力忍住悲伤,说出本剧最著名的那段独白。最后,万尼亚舅舅如行尸走肉般退场,索尼娅仰卧在工作台上。灯光逐渐扩大照射范围,点亮大半个舞台,但索尼娅被遗留在黑暗中。这似乎是在表明,索尼娅将在死后的世界里看到“布满钻石的天空”。
图米纳斯又一次展现出他把希望与哀伤交融于同一场面的非凡能力。索尼娅对光明的期待、对未来的信念,不能否定万尼亚舅舅当下的痛苦;万尼亚舅舅生命意义的丧失,亦不能否定索尼娅的隐忍和奉献蕴含着的神圣性与超越性。契诃夫对“应当如何生活”的深邃思考,在图米纳斯的诗意与梦幻中浮现。
不同于《海鸥》中的“海鸥”、《三姐妹》中的“莫斯科”、《樱桃园》中的“樱桃园”,契诃夫并未在《万尼亚舅舅》中设置一个统摄全剧的意象。图米纳斯在舞台后部放置了一座狮子雕像,它自始至终不曾被移动,或许表征着图米纳斯对《万尼亚舅舅》的总体性印象。俄罗斯评论界一般将这座雕像理解为某种历史荣耀或是权力,剧中人和它的并置,隐喻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之间的对峙。演出谢幕时,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那头狮子是图米纳斯的在天之灵,默默守护着舞台;它也是契诃夫的在天之灵,带着冷峻的微笑,提醒我们以信仰和勇气对抗生活中的种种蒙昧与荒谬。



打开APP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