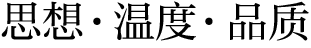杨少华去世:留下一种风格 看到几个问题
北京青年报
2025-07-18 02:57

010
◎辛酉生
 图片来源/天津市曲艺团
图片来源/天津市曲艺团
 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
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
 图片来源/中新网
图片来源/中新网
7月9日,著名相声演员杨少华去世,享寿94岁。公开报道中这样叙述他的经历:北京人,早岁在启明茶社学艺,师从郭荣启。1951年至天津做钳工,后调入南开区曲艺团。20世纪70年代进入天津市曲艺团,曾为马三立父子捧哏。
杨少华并不像年龄略长于他的高英培、苏文茂,我们能从录音资料中了解二位早年的艺术风貌。杨少华早年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他年轻时“活”使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关于他早年的学艺经历、到天津后为养家外出撂地等轶事,也多是从他后来参加的访谈节目中了解到的。杨少华真正为公众熟悉时,已经是个老人了。
光彩留给后半生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杨少华作品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为马氏父子等捧哏阶段;90年代和赵伟洲合作阶段;2000年前后与其子杨议合作并获奖阶段;2004年,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面世,转战影视阶段。“杨光系列”结束后,年过八旬的杨少华虽然时不常参加些节目录制或登台表演几个段子,但基本是玩票性质了。
在与马氏父子等人的合作阶段,现在能见到的主要资料有他与马三立合作的《开粥厂》《练气功》,与马志明合作的《地理图》《戒烟》,但这几个作品显然算不上精彩。
他与马三立合作的《开粥厂》是被讨论较多的。在这段作品中杨少华的话很少,许多该捧哏“递腿儿”(捧哏演员通过台词为逗哏演员铺垫包袱,推动情节发展)的地方都由逗哏的马三立自己翻包袱,杨少华只用表情辅助。《练气功》也有同样问题,杨少华仅在开头说了两句话,后面完全就像听了一段马三立的单口。
通过不多的资料,能够感觉到马、杨二人的合作不在平等的层面,马三立“欺”着杨少华,这显然和马三立与张庆森、赵佩茹、王凤山合作呈现的状态不一样。特别是赵佩茹与马三立的合作,就如京剧演出中旗鼓相当的演员同台,都使出看家的本领“卯上了”。
杨少华和马志明合作同样没有特别出色的作品,都没能展示各自的最佳状态,杨少华著名的蔫哏艺术也几乎没有施展。《戒烟》放在一众同类作品中,立意、包袱、人物设计都不出众。马志明塑造的爱抽烟的“前门他爸”,远不及《纠纷》中的丁文元和王德成、《夜来麻将声》中的马科长和小幺儿等人物立体鲜活。相比在新相声中谢天顺给马志明捧哏时丝丝入扣的参与感,杨少华的捧哏只能算正常完成任务。两人合作的传统节目《地理图》时长压得很短,语速很快,主要是听马志明的贯口。
1991年前后,杨少华到了退休的年纪,此时他应已开启了北漂生涯。他在这个时期印制了一张名片,上写“杨少华 全国不著名的相声演员 看完就扔”,其中的自嘲不言而喻。
量身定制以“蔫”成名
20世纪90年代初,杨少华的合作伙伴是兼具创作和表演才华的赵伟洲。赵伟洲的表演风格在网上被喜爱他的观众戏称为“犯狗”,大体上指一种使用“洒狗血”的表演配合语言蔫坏的相声表演方式。赵伟洲的这一风格和杨少华的“蔫”正是绝配。
两人的合作让杨少华真正成为广为人知的相声演员。这些作品多由赵伟洲创作,明显将包袱和人物塑造的分量向杨少华倾斜,贴着杨少华写,着力塑造他蔫坏老头的形象。《枯木开花》中要找后老伴的杨少华喊出了“我要开花”的名言;《一举成名》里,在虚构的《世界名人》杂志社撰稿人赵伟洲笔下,编造出一个斗败了野狗、在撒哈拉沙漠里嚼了皮鞋、吃了牛粪的“道貌岸然的杨少华”。时隔二三十年,这段相声仍在互联网上广为传布,二人创造的炸裂名场面被津津乐道。在《聘文书》《文坛赝品》等作品中,虽然人物塑造重点是赵伟洲扮演的不学无术的土大款,但给了杨少华对土大款进行批判的空间,更充分发挥了他“瞪谝踹卖”的技巧。
杨少华和赵伟洲的合作几乎都是平哏(以说为主)、子母哏(逗哏与捧哏两人以对等角色通过争辩、互动推进情节并制造笑料)。杨少华的艺术特点要想充分展现,非此类作品不可。惜乎杨少华不再与赵伟洲合作后,也没有了“蔫狗合璧”碰撞出的火花。
在与儿子杨议合作的阶段,杨议很注重父子身份设定的把控。这种只有父子间才能成立的包袱,一方面很受演员身份的限制,一方面又很独特讨巧。如:
杨议:我是儿子。
杨少华:我是爸爸。
杨议:我没跟您争。
杨少华:我也没跟你争。我争这干什么!
杨少华和赵伟洲、杨议合作成功的基本都是新创作品,而且都是锚定演员自身表演风格和身份特征而作,换作其他演员恐怕很难演出同样效果。这就涉及一个关于相声的论断:一段传统相声可以成为很多演员的表演作品甚至代表作,而新编相声缺乏这样的通用性。这一观点显然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作对相声演员的重要性,忽视创作,尤其在当下热衷于堆砌网络碎包袱,于相声艺术、于演员个体都没有好处。
随杨议转战影视的杨少华,用其扮演的角色杨丰年为演艺生涯留下最后的华彩。《杨光的快乐生活》成为天津的一张名片,“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也成为天津人性格的鲜活注脚。
与互联网和短视频相遇
随着年龄增长,杨少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却又碰上了互联网时代。
短视频平台的兴盛,催生了一众“互联网相声评论家”,或者也可以称为“相声周边评论家”。他们谈论的话题多为相声行业所谓的秘辛和演员间的恩怨。“评论家”们又和饭圈紧密结合,甚至发生拉踩、对立、围攻、举报等情况。面对网络舆论场的火爆,一些相声演员也下场爆料、喊话。互联网、短视频中的相声界是真热闹,但热闹得不阳光,甚至和相声艺术本身无关。在这种氛围里,杨少华作为知名相声演员,也难免被“评论家”消费。
师承问题总是短视频相声评论中的顶流话题,仿佛师承是决定一个相声演员艺术成就高低或者一个演员能不能算相声演员的先决条件,也成了一些演员树立自身权威、地位的工具。然而对于一个成熟的、有代表作的相声演员,是否有过严格的传统拜师仪式,有多大意义?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根本不从事相声表演的人,摆知(相声拜师仪式)、有“引保代(相声拜师仪式上的重要角色)”见证,又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评论家”们来说,只要话题和情绪能吸引公众眼球,就有意义。
去年夏天,互联网上的相声界发生了一波纷争,各方下场,剧情数度反转,带来巨大流量,讲的是理,带的是货。时隔一年,杨少华先生的后事也成了这次纷争的余续,谁到场谁没到场、送不送花圈,仿佛也微妙起来。
这再次让人见识了互联网的影响力,也看到了许多困在流量焦虑中的人。一个个举起的手机同步传播着现场画面,自媒体博主们忙着剪辑现场画面、评论来宾,说着“一路走好”,但似乎没见谁好好讲讲杨少华的哪段作品感染了他、影响了他。网上评价他的文章多是千篇一律,按照统一文本说他和马志明合作的《戒烟》《地理图》为经典,但是有谁在发布信息前耐心听一听这两段作品,判断一下它们在杨少华的艺术生涯中到底算不算精品?
静下心来听一段相声,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图片来源/天津市曲艺团
图片来源/天津市曲艺团 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
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 图片来源/中新网
图片来源/中新网7月9日,著名相声演员杨少华去世,享寿94岁。公开报道中这样叙述他的经历:北京人,早岁在启明茶社学艺,师从郭荣启。1951年至天津做钳工,后调入南开区曲艺团。20世纪70年代进入天津市曲艺团,曾为马三立父子捧哏。
杨少华并不像年龄略长于他的高英培、苏文茂,我们能从录音资料中了解二位早年的艺术风貌。杨少华早年似乎没有留下任何资料,他年轻时“活”使得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关于他早年的学艺经历、到天津后为养家外出撂地等轶事,也多是从他后来参加的访谈节目中了解到的。杨少华真正为公众熟悉时,已经是个老人了。
光彩留给后半生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杨少华作品大概可以分成四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为马氏父子等捧哏阶段;90年代和赵伟洲合作阶段;2000年前后与其子杨议合作并获奖阶段;2004年,电视剧《杨光的快乐生活》面世,转战影视阶段。“杨光系列”结束后,年过八旬的杨少华虽然时不常参加些节目录制或登台表演几个段子,但基本是玩票性质了。
在与马氏父子等人的合作阶段,现在能见到的主要资料有他与马三立合作的《开粥厂》《练气功》,与马志明合作的《地理图》《戒烟》,但这几个作品显然算不上精彩。
他与马三立合作的《开粥厂》是被讨论较多的。在这段作品中杨少华的话很少,许多该捧哏“递腿儿”(捧哏演员通过台词为逗哏演员铺垫包袱,推动情节发展)的地方都由逗哏的马三立自己翻包袱,杨少华只用表情辅助。《练气功》也有同样问题,杨少华仅在开头说了两句话,后面完全就像听了一段马三立的单口。
通过不多的资料,能够感觉到马、杨二人的合作不在平等的层面,马三立“欺”着杨少华,这显然和马三立与张庆森、赵佩茹、王凤山合作呈现的状态不一样。特别是赵佩茹与马三立的合作,就如京剧演出中旗鼓相当的演员同台,都使出看家的本领“卯上了”。
杨少华和马志明合作同样没有特别出色的作品,都没能展示各自的最佳状态,杨少华著名的蔫哏艺术也几乎没有施展。《戒烟》放在一众同类作品中,立意、包袱、人物设计都不出众。马志明塑造的爱抽烟的“前门他爸”,远不及《纠纷》中的丁文元和王德成、《夜来麻将声》中的马科长和小幺儿等人物立体鲜活。相比在新相声中谢天顺给马志明捧哏时丝丝入扣的参与感,杨少华的捧哏只能算正常完成任务。两人合作的传统节目《地理图》时长压得很短,语速很快,主要是听马志明的贯口。
1991年前后,杨少华到了退休的年纪,此时他应已开启了北漂生涯。他在这个时期印制了一张名片,上写“杨少华 全国不著名的相声演员 看完就扔”,其中的自嘲不言而喻。
量身定制以“蔫”成名
20世纪90年代初,杨少华的合作伙伴是兼具创作和表演才华的赵伟洲。赵伟洲的表演风格在网上被喜爱他的观众戏称为“犯狗”,大体上指一种使用“洒狗血”的表演配合语言蔫坏的相声表演方式。赵伟洲的这一风格和杨少华的“蔫”正是绝配。
两人的合作让杨少华真正成为广为人知的相声演员。这些作品多由赵伟洲创作,明显将包袱和人物塑造的分量向杨少华倾斜,贴着杨少华写,着力塑造他蔫坏老头的形象。《枯木开花》中要找后老伴的杨少华喊出了“我要开花”的名言;《一举成名》里,在虚构的《世界名人》杂志社撰稿人赵伟洲笔下,编造出一个斗败了野狗、在撒哈拉沙漠里嚼了皮鞋、吃了牛粪的“道貌岸然的杨少华”。时隔二三十年,这段相声仍在互联网上广为传布,二人创造的炸裂名场面被津津乐道。在《聘文书》《文坛赝品》等作品中,虽然人物塑造重点是赵伟洲扮演的不学无术的土大款,但给了杨少华对土大款进行批判的空间,更充分发挥了他“瞪谝踹卖”的技巧。
杨少华和赵伟洲的合作几乎都是平哏(以说为主)、子母哏(逗哏与捧哏两人以对等角色通过争辩、互动推进情节并制造笑料)。杨少华的艺术特点要想充分展现,非此类作品不可。惜乎杨少华不再与赵伟洲合作后,也没有了“蔫狗合璧”碰撞出的火花。
在与儿子杨议合作的阶段,杨议很注重父子身份设定的把控。这种只有父子间才能成立的包袱,一方面很受演员身份的限制,一方面又很独特讨巧。如:
杨议:我是儿子。
杨少华:我是爸爸。
杨议:我没跟您争。
杨少华:我也没跟你争。我争这干什么!
杨少华和赵伟洲、杨议合作成功的基本都是新创作品,而且都是锚定演员自身表演风格和身份特征而作,换作其他演员恐怕很难演出同样效果。这就涉及一个关于相声的论断:一段传统相声可以成为很多演员的表演作品甚至代表作,而新编相声缺乏这样的通用性。这一观点显然有待商榷,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作对相声演员的重要性,忽视创作,尤其在当下热衷于堆砌网络碎包袱,于相声艺术、于演员个体都没有好处。
随杨议转战影视的杨少华,用其扮演的角色杨丰年为演艺生涯留下最后的华彩。《杨光的快乐生活》成为天津的一张名片,“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也成为天津人性格的鲜活注脚。
与互联网和短视频相遇
随着年龄增长,杨少华逐渐淡出公众视野,却又碰上了互联网时代。
短视频平台的兴盛,催生了一众“互联网相声评论家”,或者也可以称为“相声周边评论家”。他们谈论的话题多为相声行业所谓的秘辛和演员间的恩怨。“评论家”们又和饭圈紧密结合,甚至发生拉踩、对立、围攻、举报等情况。面对网络舆论场的火爆,一些相声演员也下场爆料、喊话。互联网、短视频中的相声界是真热闹,但热闹得不阳光,甚至和相声艺术本身无关。在这种氛围里,杨少华作为知名相声演员,也难免被“评论家”消费。
师承问题总是短视频相声评论中的顶流话题,仿佛师承是决定一个相声演员艺术成就高低或者一个演员能不能算相声演员的先决条件,也成了一些演员树立自身权威、地位的工具。然而对于一个成熟的、有代表作的相声演员,是否有过严格的传统拜师仪式,有多大意义?一个名不见经传甚至根本不从事相声表演的人,摆知(相声拜师仪式)、有“引保代(相声拜师仪式上的重要角色)”见证,又有什么意义?但是对于“评论家”们来说,只要话题和情绪能吸引公众眼球,就有意义。
去年夏天,互联网上的相声界发生了一波纷争,各方下场,剧情数度反转,带来巨大流量,讲的是理,带的是货。时隔一年,杨少华先生的后事也成了这次纷争的余续,谁到场谁没到场、送不送花圈,仿佛也微妙起来。
这再次让人见识了互联网的影响力,也看到了许多困在流量焦虑中的人。一个个举起的手机同步传播着现场画面,自媒体博主们忙着剪辑现场画面、评论来宾,说着“一路走好”,但似乎没见谁好好讲讲杨少华的哪段作品感染了他、影响了他。网上评价他的文章多是千篇一律,按照统一文本说他和马志明合作的《戒烟》《地理图》为经典,但是有谁在发布信息前耐心听一听这两段作品,判断一下它们在杨少华的艺术生涯中到底算不算精品?
静下心来听一段相声,似乎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打开APP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