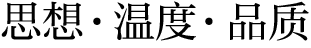再读吴冠中其画与其话
北京青年报
2025-07-03 02:35

011
◎王志
展览:我负丹青——吴冠中艺术展
展期:2025.5.30-9.7
地点:深圳美术馆
“我负丹青——吴冠中艺术展”在深圳美术馆开展以来,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来。观众们纷纷在自媒体平台分享看展照片。与此同时,新中式茶饮品牌把吴冠中彩墨画的图案元素印在了纸杯和纸袋上,从美术馆里走出来,还在回味刚才看的展,路遇一家饮品店,买了一杯奶茶,发现杯子的印花竟然是刚才看过的画。这个场景最显见的意思莫过于吴冠中的画深受大家喜爱。
的确,吴冠中的艺术深入人心,不仅成年人喜欢,此次展厅里有不少小朋友。展览特设儿童友好区,几幅色彩鲜艳的画挂得比较低,小孩子们不用家长举高,站在地上就能欣赏到。这也可以看成艺术家理念的延伸——把作品给更多人看。在吴冠中看来,好作品要“专家鼓掌”,也要“群众点头”。

 吴冠中《眼》2009年布面油彩 80×80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眼》2009年布面油彩 80×80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村》1986年纸本水墨设色 68×69cm 深圳美术馆藏
吴冠中《村》1986年纸本水墨设色 68×69cm 深圳美术馆藏
 吴冠中《形变》2007年 纸本水墨设色 48×60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形变》2007年 纸本水墨设色 48×60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窗外无月》2007年纸本水墨设色 59×48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窗外无月》2007年纸本水墨设色 59×48cm 浙江美术馆藏
艺术成就无需多言
吴冠中的画深受喜爱,这一点也体现在拍卖市场上。1989年5月,纸本彩墨画《高昌遗址》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87万港元成交,创下在世中国画家的国际拍卖纪录。2016年,他的巨幅油画《周庄》以2.36亿港元成交,不仅创造了吴冠中本人作品的拍卖纪录,同时也刷新了中国现当代油画的世界拍卖纪录。
作品在拍卖市场获得成功本来是一件幸运的事,不曾想,这也给吴冠中带来了困扰:赝品曾几度流转。对此,吴冠中深恶痛绝,上诉法院。此外,1991年9月,他整理家中保存的作品,不满意者一律淘汰,烧毁油彩、水墨、水彩画共计两百余幅——他说这无异于父母亲手终结病儿的生命。在我们看来,也许他是为了防止他所认为的次品流转到市场上。
吴冠中艺术成就卓著,这一点无需多言。他在“油画的中国化”和“水墨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画讲求形式美,他把点、线、面,黑、白、灰,黄、绿、红这几组绘画元素运用得宜,他的艺术风格鲜明可辨。
与他卓越的艺术成就相辅相成的,是他的个性与风采。他的法国老师苏弗尔皮说:艺术有两条道路,小路艺术娱人,大路艺术撼人。与吴冠中令人愉快的绘画艺术相比,吴冠中其人并不那么讨喜,甚至他的诸多言论在美术界引发长时间的争论,这也从侧面说明他活出了真性情,活成了生动的人。他的画、他的文章、他的思想以及他特立独行甚至不留情面的言行,融合成一个澄澈明净的意象,而这或许可以看作他更大的艺术成就。
这一次,不说他的画,只说说他的言行。
标题党之嫌的“笔墨等于零”
吴冠中引发强烈反响的文章首推《笔墨等于零》。这篇文章先于1992年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读者甚少,直到1997年在《中华文化报》上全文发表,这才引人瞩目。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属于“标题党”,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读到标题大概就会嗤之以鼻。
实际上,文章的意思很明白:反对孤立地把笔墨作为品评绘画优劣的标准,笔墨等绘画的媒介材料应该服务于思想感情的表达,服务于作品的整体形态及其内涵。吴冠中在文中说:“……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情思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手法永远跟着变换形态,无从考虑将呈现何种体态面貌。也许将被咒骂失去了笔墨,其实失去的只是笔墨的旧时形式,真正该反思的应是作品的整体形态及其内涵是否反映了新的时代面貌。”在另一篇回忆文章里,他重申立场:“我不是轻视笔墨,我只认为笔墨是随画面思想感情的发展而发展的,如果用程式的笔墨来套画,那么就会套在程式里得不到发展。”
吴冠中从未全盘否定中国画。他在1936年至1942年就读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随校迁徙,其间临摹中国画,并且转入国画系师从潘天寿学习一年,他也明确表示过对八大山人和石涛绘画的喜爱。
在《笔墨等于零》这篇文章里,他也谈到几类笔墨的特色:“屋漏痕因缓慢前进中不断遇到阻力,其线之轨迹显得苍劲坚挺,用这种线表现老梅干枝、悬崖石壁、孤松矮屋之类别有风格,但它替代不了米家云山湿漉漉的点或倪云林的细瘦俏巧的轻盈之线。”从中可见吴冠中对各家笔墨的不同感受。
与吴冠中在同一学院任教的中国画家张仃发表《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关于“笔墨等于零”》等文章,看起来和吴冠中形成了争论。在张仃看来,中国画的笔墨或点、皴、线条通常是值得玩味的对象,笔墨程式有“内美”,因而不等于零。又说:“笔墨并非毛笔加墨汁,笔墨是由人的创造而实现的,它是主观的,有生命、有气息、有情趣、有品、有格,因而笔墨有哲思,有禅意,因而它是文化、是精神的。”根据张仃的理解,笔墨是一种精神化了的、人格化了的、情绪化了的物质,认定笔墨的价值就是守住中国画的底线。
吴冠中和张仃关于笔墨的论述,各有各的理。有人沿张仃的思路指出,吴冠中所说的笔墨和张仃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吴冠中的笔墨指诸如斧劈皴、兰叶描之类的中国画的技法以及媒介材料,张仃的笔墨是指涵盖了技法、材料的艺术精神——因而二者的论争不在同一个层面展开,风马牛不相及。
研究者马萧进一步指出,吴、张二人因出发点不一致而引起误会,吴冠中讲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张仃偏重统一一面并且强调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二人的论争“实际是中西之争,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侧重点之争,是艺术的特殊性与普适性之争”。
忽略标题党的嫌疑,吴冠中“笔墨等于零”的提法同样彰显了其斩钉截铁、直言不讳、无所畏惧的讲话方式和性格特点。因为他直抒胸臆,一片赤诚,所以话说得底气十足。
一辈子作画做人“风筝不断线”
吴冠中1983年发表的创作笔记《风筝不断线》是他对自己艺术生涯创作思路的精辟总结。概括起来,吴冠中的“风筝不断线”大概有两种意义:从艺术创作着眼,指他的绘画与启发创作的生活场景、源头或母体之间一线牵,不至于飞太远、飞到纯粹抽象的境地而变成断线的风筝;从艺术欣赏着眼,指他的画与人民大众的感情交流一线牵,不至于离生活太远、让人看不出作品和生活的联系。
他还借用英国美术史学者迈克尔·苏立文的说法,把“抽象”和“无形象”区别开来:抽象指“从自然物象中抽出某些形式”,八大山人的作品、赵无极的油画和吴冠中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无形象则与自然物象无任何联系,是几何形的纯形式,如蒙德里安的作品。用我们今天通常的话说,吴冠中和苏立文所说的“无形象”是纯抽象,而“抽象”则昭示着另一种现代绘画——意象绘画。
在学者彭锋看来,吴冠中的画属于意象绘画,意象绘画介于具象绘画和抽象绘画之间。意象绘画和具象绘画不同,前者有更多的抽象和提炼,后者更忠实于对客观物象的描绘;意象绘画也不同于抽象绘画,前者与客观现实仍有联系,后者与现实全然无关。断线的风筝就是抽象绘画,飞不起来趴在地上的风筝就是具象绘画。
吴冠中明确表示“更喜爱不断线的风筝”,他追求的是意象绘画或半抽象绘画,而不是无形象绘画或纯抽象绘画。按吴冠中的看法,现代意象绘画既要冲破写实传统,又要发展或突破中国绘画的笔墨传统,让艺术创作从最诚挚的感受出发,去追踪和表达它。
2006年12月,87岁的吴冠中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港中大校长在致辞中说:“吴冠中先生在中国水墨画与西方油画两大传统之间,另辟蹊径,树立独特的个人画风,为国际画坛开创了一番新气象。”吴冠中坦言:“站在这里,我心情喜悦,但更惶恐。社会不会去培养诗人和画家;而是当诗人和画家的成果震撼了社会,他们才能得到认可。深深感谢这个荣誉,它推进了社会的前进。”
在生命中最后的四年里,吴冠中将自己的作品一批一批捐给各地政府,捐给人民。他曾说:“我生活在十几亿人民的国度,我的观众是广大的人民,我竭力要求自己能被他们逐步接受……我曾将作品比作风筝,出色的作品飞得高高,但她那条线联系着地面的母土,联系着人民的情愫,断了线的风筝便失去了艺术的一切。” 图源/深圳美术馆
展览:我负丹青——吴冠中艺术展
展期:2025.5.30-9.7
地点:深圳美术馆
“我负丹青——吴冠中艺术展”在深圳美术馆开展以来,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来。观众们纷纷在自媒体平台分享看展照片。与此同时,新中式茶饮品牌把吴冠中彩墨画的图案元素印在了纸杯和纸袋上,从美术馆里走出来,还在回味刚才看的展,路遇一家饮品店,买了一杯奶茶,发现杯子的印花竟然是刚才看过的画。这个场景最显见的意思莫过于吴冠中的画深受大家喜爱。
的确,吴冠中的艺术深入人心,不仅成年人喜欢,此次展厅里有不少小朋友。展览特设儿童友好区,几幅色彩鲜艳的画挂得比较低,小孩子们不用家长举高,站在地上就能欣赏到。这也可以看成艺术家理念的延伸——把作品给更多人看。在吴冠中看来,好作品要“专家鼓掌”,也要“群众点头”。

 吴冠中《眼》2009年布面油彩 80×80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眼》2009年布面油彩 80×80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村》1986年纸本水墨设色 68×69cm 深圳美术馆藏
吴冠中《村》1986年纸本水墨设色 68×69cm 深圳美术馆藏 吴冠中《形变》2007年 纸本水墨设色 48×60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形变》2007年 纸本水墨设色 48×60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窗外无月》2007年纸本水墨设色 59×48cm 浙江美术馆藏
吴冠中《窗外无月》2007年纸本水墨设色 59×48cm 浙江美术馆藏艺术成就无需多言
吴冠中的画深受喜爱,这一点也体现在拍卖市场上。1989年5月,纸本彩墨画《高昌遗址》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87万港元成交,创下在世中国画家的国际拍卖纪录。2016年,他的巨幅油画《周庄》以2.36亿港元成交,不仅创造了吴冠中本人作品的拍卖纪录,同时也刷新了中国现当代油画的世界拍卖纪录。
作品在拍卖市场获得成功本来是一件幸运的事,不曾想,这也给吴冠中带来了困扰:赝品曾几度流转。对此,吴冠中深恶痛绝,上诉法院。此外,1991年9月,他整理家中保存的作品,不满意者一律淘汰,烧毁油彩、水墨、水彩画共计两百余幅——他说这无异于父母亲手终结病儿的生命。在我们看来,也许他是为了防止他所认为的次品流转到市场上。
吴冠中艺术成就卓著,这一点无需多言。他在“油画的中国化”和“水墨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画讲求形式美,他把点、线、面,黑、白、灰,黄、绿、红这几组绘画元素运用得宜,他的艺术风格鲜明可辨。
与他卓越的艺术成就相辅相成的,是他的个性与风采。他的法国老师苏弗尔皮说:艺术有两条道路,小路艺术娱人,大路艺术撼人。与吴冠中令人愉快的绘画艺术相比,吴冠中其人并不那么讨喜,甚至他的诸多言论在美术界引发长时间的争论,这也从侧面说明他活出了真性情,活成了生动的人。他的画、他的文章、他的思想以及他特立独行甚至不留情面的言行,融合成一个澄澈明净的意象,而这或许可以看作他更大的艺术成就。
这一次,不说他的画,只说说他的言行。
标题党之嫌的“笔墨等于零”
吴冠中引发强烈反响的文章首推《笔墨等于零》。这篇文章先于1992年在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读者甚少,直到1997年在《中华文化报》上全文发表,这才引人瞩目。今天看来,这篇文章属于“标题党”,从事中国画创作的人读到标题大概就会嗤之以鼻。
实际上,文章的意思很明白:反对孤立地把笔墨作为品评绘画优劣的标准,笔墨等绘画的媒介材料应该服务于思想感情的表达,服务于作品的整体形态及其内涵。吴冠中在文中说:“……笔墨只是奴才,它绝对奴役于作者思想情绪的表达。情思在发展,作为奴才的笔墨手法永远跟着变换形态,无从考虑将呈现何种体态面貌。也许将被咒骂失去了笔墨,其实失去的只是笔墨的旧时形式,真正该反思的应是作品的整体形态及其内涵是否反映了新的时代面貌。”在另一篇回忆文章里,他重申立场:“我不是轻视笔墨,我只认为笔墨是随画面思想感情的发展而发展的,如果用程式的笔墨来套画,那么就会套在程式里得不到发展。”
吴冠中从未全盘否定中国画。他在1936年至1942年就读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随校迁徙,其间临摹中国画,并且转入国画系师从潘天寿学习一年,他也明确表示过对八大山人和石涛绘画的喜爱。
在《笔墨等于零》这篇文章里,他也谈到几类笔墨的特色:“屋漏痕因缓慢前进中不断遇到阻力,其线之轨迹显得苍劲坚挺,用这种线表现老梅干枝、悬崖石壁、孤松矮屋之类别有风格,但它替代不了米家云山湿漉漉的点或倪云林的细瘦俏巧的轻盈之线。”从中可见吴冠中对各家笔墨的不同感受。
与吴冠中在同一学院任教的中国画家张仃发表《守住中国画的底线》《关于“笔墨等于零”》等文章,看起来和吴冠中形成了争论。在张仃看来,中国画的笔墨或点、皴、线条通常是值得玩味的对象,笔墨程式有“内美”,因而不等于零。又说:“笔墨并非毛笔加墨汁,笔墨是由人的创造而实现的,它是主观的,有生命、有气息、有情趣、有品、有格,因而笔墨有哲思,有禅意,因而它是文化、是精神的。”根据张仃的理解,笔墨是一种精神化了的、人格化了的、情绪化了的物质,认定笔墨的价值就是守住中国画的底线。
吴冠中和张仃关于笔墨的论述,各有各的理。有人沿张仃的思路指出,吴冠中所说的笔墨和张仃所说的不是一回事——吴冠中的笔墨指诸如斧劈皴、兰叶描之类的中国画的技法以及媒介材料,张仃的笔墨是指涵盖了技法、材料的艺术精神——因而二者的论争不在同一个层面展开,风马牛不相及。
研究者马萧进一步指出,吴、张二人因出发点不一致而引起误会,吴冠中讲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张仃偏重统一一面并且强调内容与形式不可分离,二人的论争“实际是中西之争,是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侧重点之争,是艺术的特殊性与普适性之争”。
忽略标题党的嫌疑,吴冠中“笔墨等于零”的提法同样彰显了其斩钉截铁、直言不讳、无所畏惧的讲话方式和性格特点。因为他直抒胸臆,一片赤诚,所以话说得底气十足。
一辈子作画做人“风筝不断线”
吴冠中1983年发表的创作笔记《风筝不断线》是他对自己艺术生涯创作思路的精辟总结。概括起来,吴冠中的“风筝不断线”大概有两种意义:从艺术创作着眼,指他的绘画与启发创作的生活场景、源头或母体之间一线牵,不至于飞太远、飞到纯粹抽象的境地而变成断线的风筝;从艺术欣赏着眼,指他的画与人民大众的感情交流一线牵,不至于离生活太远、让人看不出作品和生活的联系。
他还借用英国美术史学者迈克尔·苏立文的说法,把“抽象”和“无形象”区别开来:抽象指“从自然物象中抽出某些形式”,八大山人的作品、赵无极的油画和吴冠中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无形象则与自然物象无任何联系,是几何形的纯形式,如蒙德里安的作品。用我们今天通常的话说,吴冠中和苏立文所说的“无形象”是纯抽象,而“抽象”则昭示着另一种现代绘画——意象绘画。
在学者彭锋看来,吴冠中的画属于意象绘画,意象绘画介于具象绘画和抽象绘画之间。意象绘画和具象绘画不同,前者有更多的抽象和提炼,后者更忠实于对客观物象的描绘;意象绘画也不同于抽象绘画,前者与客观现实仍有联系,后者与现实全然无关。断线的风筝就是抽象绘画,飞不起来趴在地上的风筝就是具象绘画。
吴冠中明确表示“更喜爱不断线的风筝”,他追求的是意象绘画或半抽象绘画,而不是无形象绘画或纯抽象绘画。按吴冠中的看法,现代意象绘画既要冲破写实传统,又要发展或突破中国绘画的笔墨传统,让艺术创作从最诚挚的感受出发,去追踪和表达它。
2006年12月,87岁的吴冠中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港中大校长在致辞中说:“吴冠中先生在中国水墨画与西方油画两大传统之间,另辟蹊径,树立独特的个人画风,为国际画坛开创了一番新气象。”吴冠中坦言:“站在这里,我心情喜悦,但更惶恐。社会不会去培养诗人和画家;而是当诗人和画家的成果震撼了社会,他们才能得到认可。深深感谢这个荣誉,它推进了社会的前进。”
在生命中最后的四年里,吴冠中将自己的作品一批一批捐给各地政府,捐给人民。他曾说:“我生活在十几亿人民的国度,我的观众是广大的人民,我竭力要求自己能被他们逐步接受……我曾将作品比作风筝,出色的作品飞得高高,但她那条线联系着地面的母土,联系着人民的情愫,断了线的风筝便失去了艺术的一切。” 图源/深圳美术馆



打开APP阅读全文